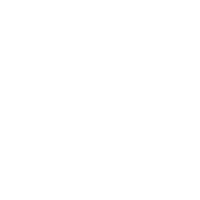永 遠(yuǎn) 的 記 憶
永 遠(yuǎn) 的 記 憶
孫知行 劉 軍
序
我們是1960級內(nèi)蒙古藝術(shù)學(xué)校的學(xué)生,我在美術(shù)班,劉軍在舞蹈班。一晃40多年過去了,現(xiàn)在我們都已先后退休,因?yàn)閮蓚€女兒都在北京工作,為了避免太多的牽掛,在孩子們的勸說下,我們便來到她們身邊生活。孩子的牽掛少了,可那老地方,那片熱土總還有許多割舍不去的懷戀,尤其當(dāng)回憶起早年在藝校學(xué)習(xí)生活的件件往事和那些深刻在腦海里的一張張師生的面孔,一串串熟悉的名字,每每令我們興奮不已,夜不成寐,有時(shí)懷舊之情來得那么急切。
剛到北京那年春節(jié),為了尋訪上世紀(jì)60年代初藝校的故交,我倆從南五環(huán)外跑到北六環(huán)外,單程就走了3個多小時(shí),目的僅僅是為了晤一面,敘敘舊。今年元宵節(jié)剛過,意外地接到了沙痕老師的電話,當(dāng)?shù)弥苍诒本r(shí),“他鄉(xiāng)遇故知”的那種難于言狀的感覺油然而生,放下電話,我和劉軍就立刻進(jìn)城與他們相聚,話題最多的依然是說不完道不盡的當(dāng)年往事和對那時(shí)師生的關(guān)切。
是啊,母校哺育了當(dāng)年風(fēng)華正茂的我們,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,使我們涉足了許多人不曾有過的經(jīng)歷,產(chǎn)生出那么多令人難忘的記憶。是藝校那段學(xué)習(xí)與歷練,給了我們熱愛生活、堅(jiān)毅樂觀的品格,也為效力國家、服務(wù)社會做了準(zhǔn)備。學(xué)校已走過了50年,現(xiàn)在高樓聳立,外觀上已找不到初創(chuàng)時(shí)期的蹤影,且規(guī)格提升,規(guī)模擴(kuò)大,諸多內(nèi)涵也發(fā)生了深刻變化,我們在為學(xué)校發(fā)展祝福的同時(shí),作為上世紀(jì)60年代初的親歷者和在藝校工作了20多年的見證人,也愿重話當(dāng)年一些片斷往事,與老同學(xué)和恩師們共鳴共享,把回憶共同珍藏,與新學(xué)友、新同事相識相勉,讓歷史相互溝通。
初進(jìn)藝校
1960年8月29日,我懷著對美好未來的憧憬,第一次離開家鄉(xiāng),從鄂爾多斯來到內(nèi)蒙古藝術(shù)學(xué)校上學(xué)。下了火車已是后半夜,早一年入學(xué)的民間歌劇班學(xué)生胡漢敏接站并帶我們步行到學(xué)校。我們頂著滿天繁星,借著手電筒的光亮,順鐵路往東走。大約走了一個多小時(shí),繞過一個土崗,看見東北方向百米之外有一盞特別亮的電燈,胡漢敏說:“那就是咱們的學(xué)校”。
我們沿著小土路到了校門口,在收發(fā)室山墻上的那盞電燈光下,推開了雙扇木門。接待的同學(xué)把我領(lǐng)到東邊共同課教室最里邊的教室,說這就是美術(shù)班的臨時(shí)宿舍,先期到校的幾個同學(xué)睡得正香。我把提包輕輕放在靠門的下床上,便和衣睡了。睜開眼睛天已大亮,這天是我19歲的生日,也是我人生中新的開端,目睹了我將要投入學(xué)習(xí)生活的藝術(shù)殿堂。
整個院落由土墻圍合,院深不過百米,東西略寬一些。一進(jìn)大門正中央是一座“工”字形大禮堂,禮堂東西兩側(cè)10米外各橫著四排平房。禮堂北面是食堂。除東西四排紅磚窯洞外,都是青一色的青磚瓦房。禮堂前部東西兩側(cè)分別是圖書館和閱覽室,禮堂尾部兩側(cè)是排練室。禮堂東側(cè)四排青磚房由南而北依次是辦公室、教室和兩排教工家屬宿舍。窯洞在教室和宿舍中間。禮堂西四排青磚平房由南而北依次是兩排琴房(有單身教工住在第二排琴房)和兩排學(xué)生宿舍,窯洞在學(xué)生宿舍前。
出校門一條彎曲小路向西南延伸,繞過土崗南側(cè)上大路入新城東門。土崗上立著一座據(jù)說是日本人修建的飛機(jī)場瞭望塔。靠近校門兩側(cè),開辟出一片不大的運(yùn)動場。南側(cè)是土坯場,再往南幾十米外是望不到邊的高粱、玉米地。向西望,是幾百米外的綏遠(yuǎn)古城墻,城墻北端聳立著一座角樓,有士兵在城墻上巡邏站崗,日夜守衛(wèi)著墻內(nèi)的內(nèi)蒙古黨委大院。
土崗上有10幾個墳冢散落在荒草中,荒草地一直延伸到古城墻下。土崗南邊是一片低洼的蘆葦塘,水塘邊上有一座破舊的奶奶廟。學(xué)校北墻外隔一條土路是內(nèi)蒙古外貿(mào)汽車隊(duì),再北是京包鐵路和大青山……置身這荒郊之外,不免有些惆悵。惆悵歸惆悵,一個農(nóng)村的孩子能到自治區(qū)首府學(xué)習(xí)自己鐘愛的專業(yè),那是一種莫大的榮幸,我開始寫日記,督促自己不輕易放過現(xiàn)實(shí)生活的每一天。
剛到校那些天,日記中寫的最多的是想家,從來沒有離開過家的我,從小就覺得只有父母的懷抱才是我最溫暖的家,此刻最讓我牽掛的是家里十分窘迫的生活,離家時(shí)已剩下合起來不足半面袋的粗雜糧,不知還能維持多久,下一次生產(chǎn)隊(duì)發(fā)放口糧是什么時(shí)候……
去武川拔麥子
9月上旬,我們還沒來得及正式上課,就按上級指示隨全校師生到武川縣支農(nóng)搶收拔麥子。我們住在一個叫東達(dá)烏素的小山溝里。每天天不亮,歌劇班的劉建忠同學(xué)就站在生產(chǎn)隊(duì)食堂的房頂上,把藝校的師生們叫起來,去食堂吃完莜面炒面、土豆稀飯,這時(shí)東方才微微泛白。武川縣地處丘陵地帶,土地貧瘠,稀疏的麥苗高不過一尺多。大家按老鄉(xiāng)教給的方法,蹲下來,左右手各把住一壟麥子,邊拔邊蹲著往前走。由于土質(zhì)松軟,倒也好拔,可是要腿臂動作協(xié)調(diào),拔得快一些,還真得練上一陣子。大家羨慕那些農(nóng)村青年,他們左右手各把兩壟麥子往前拔,一會兒就把我們遠(yuǎn)遠(yuǎn)甩在后頭。地壟特別長,從天不亮拔到中午,還是望不到麥田的盡頭。一天下來,十分疲憊。三天后,腰酸腿僵膝蓋疼,站著蹲不下,蹲下站不起來,許多同學(xué)的手勒出了血,有的戴手套,有的纏布條,有的把襪子套在手掌上,繼續(xù)堅(jiān)持。
劉軍他們跟著烏云老師在小山村里拔麥子、揀麥穗。那年她是才過12歲的小娃娃,晚上同老師睡在一盤土炕上,可能是白天干活太累了,晚上倒頭便能睡著。一天晚上,緊貼在烏云老師身邊睡著了,睡著睡著頭朝了下,枕在了烏云老師的腿上,這還不算,大膽的黃毛丫頭竟敢用手在老師的肚子上亂摸,直到把烏云老師給摸醒了。烏云老師輕輕地喊:“咳,摸甚哩!”她迷迷糊糊,眼睛也睜不開,喃喃地說:“我在拔麥子,可是怎么也抓不住”。
10多天后,公社犒勞支農(nóng)的師生,給大家吃了最好的飯食,烙油餅,炒雞蛋,16日返回學(xué)校。
上課了
9月28日,正式上了第一堂課。
國慶節(jié)后基本安定下來,按部就班地開始上課,我們也從教室搬到了禮堂西側(cè)新建成的還沒有干透的窯洞里住。10月中旬生起了火爐子。
我們班入校時(shí)26個同學(xué),有的初中畢業(yè),有的高中畢業(yè),有的還上過大專,有的已參加了工作,女同學(xué)董鳳茹為了上學(xué),給剛出生的孩子斷了奶。由于對專業(yè)的酷愛,同學(xué)們都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(xué)習(xí)生活。天不亮就去畫室畫素描,每天上午除兩節(jié)素描外,還有速寫、水彩、國畫、透視及一些文化課,下午大部分是自習(xí)。由于教室少,自習(xí)都在宿舍上。每到此時(shí),我便盤腿坐在上床,把鋪蓋卷當(dāng)桌子,上面放一塊小畫板,在那里寫寫畫畫做作業(yè)。周六下午,學(xué)生會組織發(fā)煤,同學(xué)抬著大筐領(lǐng)回一周定量的燒煤和劈柴。
當(dāng)時(shí)正逢國家困難時(shí)期的第二年,糧食、副食品及日用品供應(yīng)緊張,根據(jù)中央9月指示,城鎮(zhèn)居民的口糧減為每月24斤,布票和食油定量也有縮減。國家特別關(guān)注教師和學(xué)生的健康,口糧給予優(yōu)待。從11月1日起,學(xué)校實(shí)行分等級以人定量集體就餐制。舞蹈、晉劇武功專業(yè)及音樂吹奏專業(yè)同學(xué)的糧食定量為37斤,此外,還定期發(fā)給一些古巴糖、伊拉克棗之類的熱量補(bǔ)助,其余學(xué)生都是每月31斤。學(xué)校提倡節(jié)約,定量并不都端上桌,每月發(fā)給幾斤糧票,有的同學(xué)把節(jié)約下的糧票寄回家,有的把吃剩下的饅頭切成片晾干,準(zhǔn)備寒假帶回去,也有的小同學(xué)支援了大同學(xué)。
進(jìn)入12月,窯洞里更加陰冷,窯頂上結(jié)了白花花的冰霜,兩側(cè)靠下一些地方長出了麥芽。由于燒煤定量少,地中央的小鐵爐不敢燒得太熱,人不在時(shí),還要用濕煤面把火壓上,以保持不滅。
一天下午,我們正上自習(xí),班主任李天際老師推門進(jìn)來了,看著同學(xué)們一個不少地在聚精會神學(xué)習(xí),臉上堆滿了笑容。同學(xué)們對老師十分敬重。李老師畢業(yè)于東北魯藝,擅長國畫人物寫意,代素描課教學(xué),耐心嚴(yán)謹(jǐn)。高大的身材,風(fēng)度翩翩,黑呢子大衣早早上了身,還圍著一條長毛圍巾。這陣子他正患著感冒,鼻子和嘴常常縮捂在圍巾里,還不停地掏出手帕擤鼻涕,弄得大鼻頭總是紅紅的。
12月16日,我們班23個男同學(xué)全部搬到食堂西側(cè)把邊的大木工房,白天當(dāng)畫室,晚上是宿舍。時(shí)入隆冬,室外氣溫常常在零下20度左右,屋里雖然生著一個大火爐,也不覺暖和。剛從中央美術(shù)學(xué)院畢業(yè)來校工作的烏力格老師也和我們住在一起。他睡在遠(yuǎn)離火爐的墻角處,蓋著兩床被和一條線毯,腦門上捂著棉帽子,嘴上搭著長圍巾,只有鼻子露在外面。早晨起床,眼睫毛、眉毛和帽子圍巾邊沿都是白花花的霜。
困難的日子
1961年開春,國家到了困難時(shí)期的最困難階段,糧食、副食品、工業(yè)品進(jìn)一步短缺,買襪子、火柴也要收半個工業(yè)券。
2月25日,學(xué)校開學(xué)。學(xué)校要求全校師生同舟共濟(jì)經(jīng)受考驗(yàn),積極應(yīng)對困難。師生的口糧再次縮減,各班開班會,同學(xué)們積極申報(bào)自己節(jié)約的數(shù)量。學(xué)生的飯桌上出現(xiàn)了豆腐渣、高粱米、玉米面、玉米楂子、豆炒面等,粗雜糧的比重加大了。在那段艱苦日子里,同學(xué)們時(shí)有饑腸轆轆的感覺。
一個星期天,舞蹈小班的劉軍、白景嵐、張淑敏三人一起商量決定奢侈一回,買一點(diǎn)熟肉解解饞,她們步行去一個熟肉店,問明一斤豬頭肉是七角錢。白景嵐跟店老板說:“我買二兩,全要肥的。”張淑敏說:“我買二兩,全要瘦的。”劉軍說:“我也買二兩,要不肥不瘦的”。店老板樂了:“嘿!三個人三樣,還是這個小女女會吃”。
食堂大爺們或是采用增量法,或是粗糧細(xì)做,想辦法讓師生們吃飽吃好,于是冠以時(shí)代特征的美食名字誕生了。所謂“金銀卷”就是用玉米面和白面做成的雙色花卷,所謂“迎春米飯”就是用高粱米、紅豆、小米做成的雜糧米飯,所謂“歡樂窩頭”就是玉米面窩頭。大餐廳內(nèi)西南墻角有幾口粗矮的甕,一年四季甕里腌著醬芋頭(苤藍(lán)),沒有鮮菜時(shí),它便成了惟一的下飯菜。
學(xué)校加大了生產(chǎn)自救的力度。3月下旬,在校院外南邊開荒打井整地種菜。在東郊黑蘭不灘設(shè)了養(yǎng)殖場,養(yǎng)羊、養(yǎng)雞、種菜。勞動課正式安排進(jìn)課程表,每周有三個下午的勞動課,必要時(shí)還常常追加一些課時(shí)。
秋 收
全班去畢克齊挖土豆。到30日下午,土豆地挖了一半,從學(xué)校帶來的糧食吃完了,同學(xué)們都回了學(xué)校,留下我和樊建平、包長祿、白音倉在瓜棚里看守土豆。傍晚時(shí)分,迪之老師來說,學(xué)校拉土豆的車在一家村陷進(jìn)了泥坑,讓我們?nèi)椭铣鰜怼N覀兲嶂R燈摸黑趕往,過了兩道水渠又被一片泥塘擋住了去路,只好挽起褲管脫掉鞋,我背著迪之老師趟了過去。可車不見了蹤影,我們就繼續(xù)回瓜棚留守,攏起旺火取暖烤鞋,燒土豆充饑。
國慶節(jié)那天,天陰著,我們在畢克齊文化局農(nóng)場初識了沙痕、裘耀章、肖安南、赫歷等后來到學(xué)校工作的老師,他們都是在那場反右斗爭中被嚴(yán)重?cái)U(kuò)大化而錯劃為“右派”的一批知識分子,正集中在這里勞動。這一天他們被宣布解放了,9人一桌聚餐慶賀。沙痕老師還即興賦詩貼在院里的木樁上。晚上又下起雨來,我們和裘耀章老師擠住在一個窩棚里。
10月中上旬,校園內(nèi)的葵花、蘿卜、大蔥、大白菜到了收獲的季節(jié),各班的勞動課大都安排在這里,同學(xué)們懷著喜悅的心情收獲自己的勞動果實(shí)。
王文興老師
戴著金絲眼鏡的王文興老師給我們上語文課,他那很重的江浙口音有時(shí)聽不大懂,我們常常當(dāng)堂發(fā)問,有時(shí)課下請教,他總是笑咪咪,很耐心。一天他在講臺上寫板書時(shí),我猛然發(fā)現(xiàn)他藍(lán)棉褲屁股后面一撮棉花從破洞里掉出來,一甩一甩的,他腳上穿著的黑條絨棉鞋也打了補(bǔ)丁,大腳趾快出頭了。敬重之余,心里有點(diǎn)酸楚。后來才知道當(dāng)時(shí)他家里孩子多,生活困難。當(dāng)我也做了父親的時(shí)候,更理解他掛在臉上的笑容,多了一份內(nèi)心的希望。那笑容和那撮棉花讓我記了一輩子。1980年底,我在學(xué)校介紹他參加了黨組織。我到文化廳工作時(shí),他已被文化廳借調(diào)派到北京中央音樂學(xué)院附中內(nèi)蒙古管弦樂班做班主任,和30多位學(xué)生一起住在遠(yuǎn)離城區(qū)的西山北太舟塢農(nóng)村,負(fù)責(zé)管理學(xué)生生活與安全。
我每次到北京,總要去看他,一是工作,二是總也放心不下他們老倆口那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生活。后來他還是心力交瘁,在工作崗位上病倒了。我最后一次陪他到醫(yī)院檢查,他已病得很重了,但他還是坐在輪椅上對我說:“沒事的。”不久,他去世了。我代表文化廳和他的學(xué)生去八寶山為他送行。在我向他深深鞠躬的時(shí)候,他那笑容和那撮棉花又出現(xiàn)在我面前。秋天,我去新城西街的小平房里看望王老師的老伴顏杏先老師,她本來瘦弱的身體又蒼老了許多,惟有那深凹在眼眶里的眼睛仍然那么堅(jiān)毅,那么炯炯有神。老顏說:“我們1952年離開上海,支邊來到內(nèi)蒙古,算來有30多個年頭了。他是一個共產(chǎn)黨員,他把生命獻(xiàn)給了教育事業(yè)是光榮的,一輩子就這樣了結(jié)也很圓滿。過些日子我要回南方長住一段時(shí)間。”
困難留下的思考
物質(zhì)生活困難,生產(chǎn)勞動很多,師生團(tuán)結(jié)友愛,思想積極向上,學(xué)習(xí)奮發(fā)努力,這就是那段歲月學(xué)校主流生活的真實(shí)寫照。師生們之所以能以很高的覺悟、健康的心態(tài),從容面對艱苦生活和較多勞動,平穩(wěn)地度過困難時(shí)期,究其原因至少有三:一是年輕的共和國物質(zhì)生活原本處于低水平,心理上有足夠的承受能力,加上國家的特殊關(guān)照,困難時(shí)期覺不出太大的反差,農(nóng)村來的孩子普遍感覺甚至比家里吃得還好。說到勞動,教育方針有 “教育必須與生產(chǎn)勞動相結(jié)合”的要求,同學(xué)們從中小學(xué)都受過這樣的教育和鍛煉,熱愛勞動,吃苦耐勞,勇于實(shí)踐已是很平常的習(xí)慣與品格。勞動多并非中央所提倡,也確實(shí)耽誤了一些學(xué)習(xí)時(shí)間,但正效應(yīng)大于負(fù)效應(yīng),艱苦中得到的思想品質(zhì)和意志的鍛煉,終身受益。二是當(dāng)時(shí)社會風(fēng)氣非常好。人民群眾剛從舊社會的苦難中擺脫出來,熱愛新中國、熱愛社會主義,在“鼓足干勁,力爭上游,多快好省地建設(shè)社會主義”的總路線指引下,一心一意建設(shè)自己的新生活,夢想著早日實(shí)現(xiàn)共產(chǎn)主義。那時(shí)代的人沒有信仰危機(jī),團(tuán)結(jié)互助蔚然成風(fēng),以苦為榮,以苦為樂,艱苦奮斗是那個時(shí)代最典型的時(shí)尚。三是當(dāng)時(shí)國家處于非常時(shí)期,中華民族歷來就有在危難時(shí)期更加團(tuán)結(jié),不屈不撓,不怕任何艱難險(xiǎn)阻,勇于犧牲的民族精神。共產(chǎn)黨及其領(lǐng)袖毛澤東有著強(qiáng)大的凝聚力,困難時(shí)期,毛主席主動降低自己的生活標(biāo)準(zhǔn),人民愿與領(lǐng)袖們同甘共苦,同舟共濟(jì)。多一點(diǎn)生產(chǎn)勞動,既可為國家分憂,又可為自己解困。
還應(yīng)當(dāng)提到的是,當(dāng)時(shí)物質(zhì)生活雖然困難,但精神生活卻充實(shí)豐富。學(xué)校有整天開放的圖書館、閱覽室,有扎實(shí)有效的政治理論課和生動活潑的黨、團(tuán)、隊(duì)生活,有不定期的形勢報(bào)告、先進(jìn)典型報(bào)告、憶苦思甜報(bào)告、學(xué)術(shù)報(bào)告,有經(jīng)常性的音樂會、匯報(bào)會、結(jié)合形勢的演出實(shí)踐,還有頻繁的電影、戲劇、戲曲觀摩學(xué)習(xí),給師生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。這些活動與專業(yè)教育有機(jī)配合,營造了教書育人的良好氛圍。在最困難的1961年,學(xué)校就組織看了多場電影。除去寒暑假,幾乎周周有電影,月月有文藝觀摩,物質(zhì)生活的貧乏,得到了精神生活的補(bǔ)償。那年月酸甜苦辣有滋味,激情燃燒鍛煉人,那段時(shí)光還真值得特別懷念。